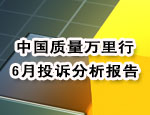中国青年报:有报道指出,当前我国医院的护理资源严重匮乏,缺口达190万人。这也是导致医生工作强度变大的原因之一吧?
周子君:是的。在西方国家,一般是1个医生配4个护士,而我们是1个医生配1.5个护士。护理资源的严重匮乏使医生经常不得不做护士的工作。不合理的医护比,使医院的护理服务和整体医疗服务都受到影响。虽然现在北京三级医院很多护士的月收入也能达到8000~10000元,但护士的劳动强度不是一般职业能比的。他们经常值夜班,要承担很多执业风险,加上社会地位较以前大幅降低,使很多年轻人不愿从事这个行业。
中国青年报: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70.7%的医师还将工作压力来源锁定在“医疗纠纷”上。对此,您怎么看?
周子君:是的,当前社会医患关系紧张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医疗服务与其他服务不同,不是病人花了钱,医生就能保证把病人治好,这一点与病人及其家属的期望有很大差异。如果花了很多钱病却没治好,有些病人和家属可能接受不了,造成医患纠纷。
另外,医生承受的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病人对医疗体制的不满。例如,一些病人看病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要忍受嘈杂、拥挤的环境,这些是跟我们的医疗体制和政策有关,与医生没有直接关系,但病人往往会将积压的不满情绪发泄到医生身上。在美国,尽管医疗费用很高,但你很少会看到病人对医生发泄不满。
中国青年报:医患关系紧张也有医生的责任吧?比如“天价医药费”等现象的出现。
周子君:不可否认一些医生的职业道德在利益驱动下出现了扭曲,但也应该认识到,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复杂的,涉及到国民素质、社会诚信、医生执业道德和媒体宣传等多方面。
近年来,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少民众遇事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比如,出现一些公共事件,大多数网民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是首先去质疑、指责他们认为有责任的一方。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改善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从国内外的医疗实践看,医院出现的绝大多数医疗差错,并非由于医务人员的素质、道德、责任心有问题,而是由于制度、规章存在缺陷。有研究显示,一味地谴责和惩戒医务人员,不仅不能实现对医疗差错的有效控制,反而可能增加患者的医疗风险和经济负担。
如今,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保护自身利益,一些医生对病人进行“过度治疗”,即使是不必要的检查,也让病人去做。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医院就能凭借专业优势,轻易摆脱干系。但这样做不仅浪费社会资源,也增加了病人的医疗费用,更重要的是“过度治疗”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风险。
中国青年报:那该如何解决医疗纠纷?
周子君:首先是要建立互信的医患关系。目前的医患关系对医患双方均有很大危害。患者处处防备医疗机构、怀疑医务人员,就不可能期待从医务人员那里得到信任;医院、医务人员一味考虑自身利益而非患者利益,同样会招致患者的质疑。因此,建立互信的医患关系,需要医务人员、患者和社会公众共同努力。公众要理解“是人就会犯错”这一理念,形成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二,我们要改革医院的付费机制,扭转医院的趋利性。今年8月,北京市开始试行医保付费制度改革,将现行的“按服务项目付费”改为“预付费”,可以有效扭转医院和医生“多做检查、多开药就能多收益”的模式,促使医生用尽量少的检查和治疗项目。
第三,我们要探索建立新型的医疗伤害赔偿制度。医疗纠纷的核心都涉及赔偿,建立公正、合理的医疗伤害赔偿制度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化解。虽然医疗伤害多数是由制度、规章,以及患者自身身体状况造成的,但患者因为医疗受伤致残,仍然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外成熟的伤残补偿制度,明确医疗伤害补偿标准,建立国家或地方医疗伤害赔偿基金,用以支付患者的医疗伤害补偿。至于由医生责任造成的伤害,自然有相关的法律来处罚医生。
最后,我们还要改变公立医院“管办不分”的状况。使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从主要维护医院和行业利益,转向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使百姓能够以较小的代价维护自身权益。(记者 肖舒楠 实习生 刘雅琴)
上一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