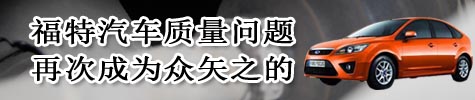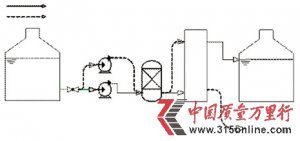【老枪/文】年年春运年年骂,今天又多了一个骂点:抢票插件。
对媒体言,每年春运都是一个可以用最廉价方式获取更多注意力的良机。只要走民粹路线,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喝彩。微博时代,连党报国社也不例外,且民粹的比市场化媒体还粹。
这个周末,抢票插件正被议论的如火如荼时,党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周六的每晚例安中写道:
【你好,明天】当抢票插件引发热议,谁又理解农民工的乡愁?他们在寒风中排起长队,票源却在网上瞬间抢购一空,高科技竟成剥夺机会的推手。给售票窗口留些车票,这么简单的方案难道想不到?关爱弱势群体,不止于廉价的同情,更在于公平的制度设计。机会公平,阶层才不至固化,社会才能存续希望。安。
但国社——新华社显然不能同意。周日,财经网微博发布的一则新华社记者述评如是说:
【新华社:铁道部工信部不能“自己傻就怨别人太聪明”】铁道部斥资3亿建起的平台竟经不起住小小网络插件冲击!自己不好好修补Bug,却忙于“约谈”和“叫停”,动用行政权力阻止市场行为。“一票难求”是旺盛需求与运力不足间的矛盾。抢票软件出现说明,有市场就挡不住有研发来填补。
一方为不会使“高科技”的农民工们仗义,一方为会用“高科技”的小白领们直言,双方背后都站立着足够庞大的群体。而且,事实上,这两者现在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屌丝群体,越来越谈不上谁比谁更有地位更强势了。如果由此引发一场“战争”,那将是一场中国社会两大屌丝群体的大对决。这恰是中国社会当前的荒诞真实。
相比较而言,国社比党报更接些地气,点出了市场供求这个要害。
但一说到市场供求,就有另一批牛人登场,他们自以为挟经济学利器,可平息天下一切纷扰繁杂:价格决定论。所谓“春运”,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造之。只要涨价,涨到供求平衡,什么叫“春运”?根本不存在!
只是,若按他们这套办,那最有回家心理与情感需求的农民工和小白领们,需求将得不到满足。而相对富裕者,则可以乘经济学长风母慈子孝天伦得圆。春节的城市,留给住工棚的民工和挤住出租屋的小白领这两大屌丝群体共享,也算是经济学带给屌丝们的福利。或者,干脆,把这类牛人称之为中国式福利经济学家。
回到问题本源。
无论非实名制下的排队购票黄牛倒票,还是实名制下的网络刷票插件抢票,所有的票,最终是有人用来坐了车。这些年来无论铁路、公路、航空,整体运力在快速增长,但春运的压力却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归根到底是人口流动增得更快。
春运有解吗?
铁路官员说,除非储存平时正常运力的10倍,否则无解。
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建设并承受这样一个运力系统吗:一年中的11个月只用10%能力,只春运这一个月用足?
显然不能。
反过来,我们可以让人口在这一个月中的流动降低90%吗?
显然不能。
那么,我们可以让这一个月里需要回家的人中的10%最富裕者满足需求,而把另90%的需求用价格门槛挡回去,让他们在春节这个情感特殊窗口期回不了家吗?
这不是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个敢不敢的问题:谁敢?
都不能,或不敢,那就无解。
要面对这个现实,在此前提下,尽量从方方面面把平衡工作做的更好些,所谓田螺壳中做道场。在这个问题上,民粹也好,经济学也罢,作为平衡社会心理的“骂器”,用用无妨,但要适可而止。
无解的春运问题,事实上是中国现行模式继续下去终将走入无解困境的先兆与缩影,更是警讯。
为什么会有春运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答案是现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
那么,再问: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怎么造成的?有解吗?
这个问题,本枪在今年的“准元旦献词”《进退改都难的时代》一文中已做过回答:
“中国的发展模式实质被决定于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模式。以中央为总核心,围绕着总核心,是省级子核心;围绕着省级子核心,是地市级子子核心;围绕着地市级子核心,是县级子子子核心。四级核心层次分明层级清晰,方向更清晰:统统以上级核心为中心点向上而指。
这一模式造成了所有资源被最大限度地为上级核心所在地吸纳。这四级核心城市与区域把几乎所有资源全部吸纳到极限,而又无力对所有随资源吸纳来的人群做相应平等公共保障。同时,更使得广大的四级核心之外的地区,因为把连人在内的资源都吸纳殆尽,而无法摆脱贫困得到发展。”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权力结构模式不作根本改革与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就无解。由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春运问题,也就当然不会有解。
更进一步的事实则是,中国的更大发展不平衡是社会整体的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由权力模式导致的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而非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这种结果的日益严峻,又反过来促使社会发展愈加不平衡。包括春运在内的所有由此所致的问题,也就更加趋于无解。
中国社会不平衡的特征是,权力核心所在之地实质上就不是现代社会,而离权力核心越远,离现代社会就更加遥远。在远离权力核心的地方,人们不仅严重缺乏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机会,更缺乏最基本的精神自我生存土壤。因此,人们不得不逃离那些远离权力核心的地方,流向各级权力核心所在。这既是寻求更高收入的必须,也是寻求更多精神慰籍的必须。但,残酷的现实却是,这些权力核心的本质是吸血而非纳新,这就使得绝大多数人成了所谓流动人口,在物质与精神上,都不得不以家乡为巢穴以工作地为就食所,如候鸟般来回“流动”。
这种不平衡的实质是中国一直把自己绑定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迟迟无法进入一个权力逐次自治的公民社会。因此,一个14亿人口之巨的国家,无法形成多中心的相对权力完整而自洽的自治区域群,使得人们在各自所居区域,都能有机会得到虽然作横向区域比较有差异甚至是较大差异,但却在区域内相对完整的自我发展可能。
理解这一点必须理解两件事:
一、多中心的、权力逐次自治的公民社会不是否定城市化。
二、人们的自我发展需求并非只有物质需求。在物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对社会事务的表达与参与需求同样重要。
权力集中的体制与模式,在30余年来,看似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说“看似”,是因为虽然有人不同意快速发展得益于权力集中,却也无法否定,因为历史无法重试。但可以通过观察如春运、如异地高考等等无解、难解问题而预言的是:
这种权力集中体制与模式的红利已越来越到尽头,继续坚持与强化下去,很可能将走向反面。渐进多元权力中心与公民社会培育发展,对使社会可持续发展来说,越来越成为必要与必须,也越来越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