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蚂蚁金服相互宝公示了今年8月第二期的成员名单,616人向另外7992.03万名参与者申请了救助,原因包括癌症、开颅、心肌梗塞等。
在北京工作的陈亮从今年年初开始关注并加入相互宝的计划,他已经帮助了727个人。32岁的陈亮发现,身边的朋友其实都有在关注相互宝这个计划。
2018年10月,支付宝在其客户端内推出相互宝。这项“大病互助计划”为符合条件,遭遇大病或严重意外的参与者,一次性给予最高30万元互助金,截至目前,吸引了8000多万人。
相比前几年,可能大多数消费者并没有听说或者了解网络互助到底是做什么的。
网络互助迎来巨头“洗牌”
网络互助计划属于“类保险产品”,是指会员之间通过约定缴纳互助金,并承担同质的风险损失,参与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即“事前预存+事后分摊”和“事前零预存+事后分摊”。无论是互联网平台,还是网络互助平台,巨大的平台流量背后,其实是保单转化的需求。
在中国,网络互助起于2015年,兴于2016年,经历了2017年的大浪淘沙之后,于2018年复苏,由于巨头的加入,2019年或许又经历一次新的洗牌。
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统计,截至2018年12月,国内11家主要网络互助平台,累积参与人数已超过1.5亿人次,累计互助金额接近11亿元。过去一年,包括支付宝背后的蚂蚁金服,多家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了互助领域。
2014年,国务院发文鼓励保险业发展提速,其中明确提出了“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2015年初,原保监会颁布《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希望通过相互保险扩大全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同时丰富了国内保险业的市场组织形式。
网络互助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由于其“类保险”的特质,不管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会有意无意将之认为是保险产品。随后,监管部门出于风险考量,将网络互助与保险界限进行严格区分。2015年10月,原保监会发布《关于“互助计划”等类保险活动的风险提示》,明确互助计划与相互保险的区分。
然而,直到今天仍有消费者会将网络互助产品联系为保险产品,特别是相互保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产生,除了保险知识、保险意识不够之外,部分网络互助从业者在对外宣传平台的时候,也存在误导消费者的情况。
2016年底,原保监会一纸《关于开展以网络互助计划形式非法从事保险业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开启“严厉监管”的闸门。彼时,网络互助平台被迅速划分为三类,一类机构允许继续探索,二、三类机构则上了负面清单,进行了约谈、整改和强制退出处理。
2016年也被称为“网络互助元年”,那一年诞生了300多家网络互助平台。接下来3年中,这个行业迅速积累起上亿用户,也爆发了破产,清退,甚至卷款跑路等众多乱象,遭监管部门屡次警示。经过几年的发展,网络互助行业已经进入3.0阶段,对用户提供更精细化的服务、把线上的服务深入到线下是“网络互助3.0”阶段特征之一。更重要的是,网络互助行业进入3.0阶段后,互助平台之间拼的其实是社群和关系,这是网络互助的本质,也是网络互助的根基。
在流量时代建立起规模壁垒后,“后流量时代”比拼的则是流量获取的效率,以及留存和复购。
另外,未来可否盈利也将成为行业的关键。今天的很多网络互助平台都处在微利或者不盈利的状态,主要原因还是和这个行业属性有关,目前行业通行做法是收取8%左右的管理费,这些费用主要用于平台的正常运营等。
“拒赔”存争议监管还需填补“空白地带”
前不久,蚂蚁金服也因为分摊费上涨的事情再次引起争议。相互宝之前曾做出承诺,2019年的单人分摊总额不会超过188元。
据相互保公示的7月份2期分摊费用公示显示,被帮助成员为496人,分摊人数7562.18万人,人均分摊1.48元,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是此前每次的分摊费用较少最多也就几毛几分,而这一次突然涨到了1.48元,相互保参与的成员越来越多了,怎么分摊费用反而越来越高了?
面对这种质疑蚂蚁金服回应媒体称:费用增加主要是因为相互宝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患病的成员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目前加入的人数已经超过80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分摊的人数增速不及帮助成员数,是导致分摊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
此外,互联网平台在追求着“普惠”“低门槛”,但规则难免有模糊的区间。当申请救助者被拒理赔,模棱两可的条款难免引发争议。
网络互助也不具备保险行业那样的线下销售人员,这些人员本可以指导用户阅读合同、健康告知,许多保险公司在保单签约前核保,避免事后再为是否符合投保条件争执。
目前在网上检索,相互宝、水滴互助等多家主流互助平台,都有因“拒赔”引发争议的案例。
据悉,相互宝试图用集体投票的方式解决争端。相互宝的8000多万用户中,目前有100多万通过了线上考试,成为了“赔审员”。在为期24小时的赔审中,他们将就是否给予救助进行投票。最终,多数方意见将决定是否给予互助金。
在2016年,原保监会曾连续3次对互助行业下发警示,整治网络互助平台没有保险资质,缺乏合法的准备金,也没有官方认可的精算环节,却给予消费者能获得近似保险般“刚性赔付”的虚假预期,甚至采用各种擦边营销手段大肆推广。
但目前,几乎所有互助平台上的发病率和人均花费,都远低于这一数字。对此,诸多平台的回应趋于一致:参与群体仍偏向熟悉互联网、高素质的年轻人群,加之严格的风控核查,因此风险较低。
这意味着,参与互助的年轻人某种意义上“补贴”了其他参与者;而且,随着互联网、移动支付进一步普及,用户年龄趋于平衡,均摊费用可能增加。
就目前而言,网络互助平台的经营主体不是具备保险经营资质的保险公司,没有被纳入金融监管范畴,其发行的互助计划也不是正规的保险产品。银保监会曾多次发布风险提示,要谨慎购买互联网平台的“保险项目”。
《南方都市报》曾于2018年展开一项调查,发现有些互助平台客服电话无人接听;还有平台标注的电话被拨通后,对方语气茫然,对所谓的平台一无所知。
值得注意的是,互助平台的成员基于契约精神,而组成互助团体,而各大互助平台由于经营理念和模式的差异性,经营状况也参差不齐,有些平台由于经营不善,最后难以持续,使用户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尽管网络互助有着诸多方面优势,但其不是商业保险,没有先收保费,无法可依。
有专家提出,大病互助形式进入我国时间并不长,由于目前国内信用体系不完善,尚未建立对于获捐者的真实情况、资金需求情况的评价标准和监督机制,尚处于监管的“空白地带”,亟待监管的介入。
在此之前,网络互助应先市场自律,平台保持自律性并制定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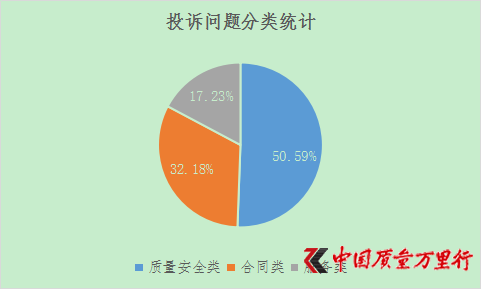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432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4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