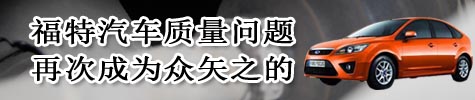多年来超适应症用药一直屡禁不止,背后除了有经济利益的直接驱动,也有许多令医学界进退两难的伦理困境。

在医药界,“试药”的不仅是“小白鼠”。
“拜瑞妥”治疗静脉血栓事件,使“超适应症用药”的医疗内幕在中国被掀开。虽然这早是医药行业“公开的秘密”,在国际上,罗氏、辉瑞、礼来等制药巨头都曾因超适应症用药被开出过巨额罚单,但在中国,至今未有一起同类案例被罚。“仁慈”的中国政策环境,能否换来国际医药巨头主动的社会责任承担?
谁也没有想到,有关“超适应症用药”的内幕会以这样的方式被踢爆。
5月,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张强率先在微博上发出质疑:“‘拜瑞妥’在欧美仅限于房颤或关节置换术的血栓预防,为何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大量拜瑞妥用于静脉血栓治疗的情况?”
张强素有“Sm ile医生”之称,在全国各地的医生博客中,其网站的点击量一直名列前茅,每天均超过4000人次,在网络上拥有大批粉丝。此番开炮,让拜瑞妥的母公司、国际制药巨头拜耳顿时陷入了舆论漩涡、猝不及防。
一家头顶光环的制药巨鳄罕见地在中国受到了商业伦理的拷问。一个生僻的医学概念———“超适应症”也开始走进公众视野。
以身试药
在中国的医疗市场,超适应症用药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想要找出蛛丝马迹并不困难。一旦深入求证,一个隐秘的群体随之浮出水面——— 试药志愿者。
26岁的刘帅坐在广州市某三甲医院心理科的诊疗室里,身上的白大褂说明了他的身份。一年前,他只是一名医学院学生,多次成功应征为试药员。“试药员”的称谓听上去带着几分惊悚,但在医学院里招募健康大学生参与人体实验却稀松平常。那些具备药理知识的年轻人往往对科学实验持开放态度,而一笔不菲的报酬也具有诱惑力。根据采血时间、试验目的以及不良反应程度的不同,受试者每次均能获得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的经济补偿,遇上需要留院观察的情况,则食宿全包。
刘帅曾先后数次参与过人体试验———体检、服药、抽血、报告。多数时候,试验过程都风平浪静、温和无比。但有一次,因服药过量,刘帅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霎那间天旋地转,头昏眼花,躺在床上久久说不出话来。虽然风险较高,但刘帅却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试药员的牺牲精神,如何能推动医学的进步和发展?”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新药上市都必须经过临床这一关。据统计,国外每个新药的平均开发费用大约为12亿美元,其中70%以上的费用都用在了临床试验上。值得一提的是,临床实验包括四个阶段,除了第四期外,前三期都必须在新药上市前完成。每一期都有对受试人群数量和种类的规定。比如,一期以20~30名健康志愿者为主,二期以患病人群为样本,到了第三期时,试验病例必须扩大到上千例。
在美国,许多治疗药物常常为找不到足够的人群参与临床研究而发愁。但在中国却不成问题。高额报酬能吸引健康志愿者,大量陷入绝望的重症患者也因为无药可治,愿意放手一搏,心甘情愿成为欧美制药企业的试验品。
另一方面,与试药相对的则是高昂的时间成本。通常一个新药仅能享有20年的专利保护期,从申请专利到临床实验再到成功上市至少需要8~12年,也就是说新药的专利期实际上平均不到10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市场———市面上有超过九成的药物均为仿制药,一旦专利到期,研发企业将面临严重的业务困难。所有欧美药物想要在中国上市,亦必须在亚洲人群中重做试验,这意味着又将有2~5年的时间被消耗掉。
也正因如此,制药巨鳄们想要依靠专利优势捞金,唯有与时间赛跑。通过提前上市,进行“超适应症推广”便是一个屡试不爽的独门秘笈。
由“拜瑞妥”引发的“口水战”
张强是清楚这一点的。近年,他专注于疑难杂症,已鲜少过问医药行业的事。只是这一回,拜瑞妥撞到了枪口上。在网站和门诊过程中,络绎不绝的病人纷纷向他求教,到底治疗血管类的静脉血栓药物是用华法林还是拜瑞妥。“这刚好是我的专业,对方又是知名的大公司。”张强一下来了兴趣。
华法林是一款经典的抗凝药物,在临床治疗上已有近60年历史。拜瑞妥则是制药巨头拜耳和强生联合开发的一款血液稀释剂,学名利伐沙班。该药2008年10月在加拿大和欧盟获批上市,2009年下半年才正式进入中国。有资料显示,拜瑞妥曾于2011年12月拿到欧洲监管机构发出的用于治疗深静脉血栓(D V T )的批准。拜耳在今年5月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也称,目前全球共46个国家批准了D V T这一适应症。
不过,张强在询问了国外同行并查询了相关资料后,并没有发现拜瑞妥有明确的关于D V T的治疗指征。实际上,直到今年11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 A )才同意扩大拜瑞妥的使用范围,包括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 V T )或肺栓塞(PE )以减少初始治疗后复发性D V T和PE的风险。而在中国,拜瑞妥获得合法批文的适应症,仅包括用于髋、膝关节置换术过程中患者血栓的预防,并未包括非骨科类的治疗。
有血管类病人向张强反映,其目前服用的拜瑞妥是自掏腰包购买的。这一说法证实了张强的判断———拜瑞妥有重大的“超适应症推广”嫌疑。因为按照惯例,所有未获批准的药物在试验阶段只能以“免费赠药”的方式提供给患者。
业内人士指出,拜瑞妥的确是近年来抗凝药物领域的一个“重磅炸弹”。与华法林相比,拜瑞妥“无需凝血监测、无需调整剂量,不受食物影响,且出血安全性上也高于华法林0 .4%”,拥有广阔的前景。对此,张强并不予否认。
但两款药物在价格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单片华法林的售价仅为0 .29元,而单片拜瑞妥的售价则高达100元,足足相差了300倍。“这就好比一个是中国的安全带,一个是英国的安全带,中国安全带的折弯率是3%,英国的是2%,但价格相差了几百倍,你说老百姓会选哪一个?”
然而,账本到了医药公司那里,就是另一种算法。“治疗领域与预防用药领域的利润差别很大。”张强指出,如果仅作为骨科预防用药,2周就是一个疗程,但是一旦在血管外科中用作治疗用药,一个疗程至少6个月,有的心血管疾病还需终身服药。“增加一个D V T适应症意味着销售市场将成几十倍地增长。”也有网友向其透露:“2011年拜瑞妥销售1亿,其中有40%的收入就来自超适应症D V T的推广。”
对张强的指控,拜耳医药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林彦向媒体表态:“拜瑞妥已经完成了在中国的三期临床试验,并且获得生产国的批准,现在只等待审批结果。公司方面是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明文禁止超适应症的市场推广活动的。但是医生获知信息的渠道很多,国外已经获批的适应症,国内医生很快就知道了。”
“言下之意是把责任推给了医生。”对此,张强很是气愤,“难道拜耳对大量超适应症(非骨科)用药至今一无所知吗?公司就没有供货信息可查?如果没有公司在相关科室铺药,医生又如何能开出药品?”
此后,张强没有继续更新微博,也拒绝再透露更多细节。“我不想再让更多医生难堪了,有些人连具体的名字都有,都是很大的主任。大家都是同行,也不容易。”他只希望能借此机会给拜耳公司一个警告。“中国给它的环境是宽松的,不是一般的宽松,是非常的宽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国际公司应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应该做一个榜样。”
隐蔽的营销“杂技”
国际上,罗氏、辉瑞、礼来等制药巨头都曾因超适应症用药被开出过巨额罚单。2009年,辉瑞擅自推广伐地考昔等四款药品的非适应症“疗效”,被罚了23亿美元;同年,礼来也因为非法推广精神药物“再普乐”的超适应症,被罚了14.2亿美元。与之相比,中国至今未有一起因超适应症用药被罚的案例,可谓相当“仁慈”。
而一部反映1997年后美国医药行业的商业模式的电影《爱情与灵药》,则再现了15年前辉瑞公司内部员工培训的场景。身着职业套装的培训主管义正词严地对台下众多新学员道:“说明书外使用药物虽有益处,但FD A并不认同。但若你能提议这种做法,将大量提升你的销售额。比如,处方药郁乐复在医理上只可医治抑郁,但说明书外的用途则有酗酒、暴食症、经前综合征、抽烟、社交恐惧。你们的职责便是分享科技、拯救生命!”
如今的制药巨鳄们经过多年的“进化”,早已淘汰了明目张胆的营销方法。医药公司的销售“杂技”演绎得更加不动声色、炉火纯青。
以召开学术会议的名义对医生们进行培训,推广药品的疗效,是业内广为人知的办法。一些医生与药厂借此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有的甚至直接成为了某种药品的代言人。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药代表就曾在一个大型医学会议上,亲眼见证某位心内科主任的巨幅海报被医药公司挂满了整个大厅,就像欢迎前来走穴的娱乐明星。会上,该主任对某款药物完全不吝溢美之辞,所有的演讲内容均是医药公司事前安排好的,带着明显的倾向性。不过,涉及“超适应症”的敏感信息并不会在这样的场合被公开提及。通常,只有私下进行同行业务交流,或者召开更小型的分享会时,这些关系匪浅的专家才会将自己“超适应症用药”的某些“成功”经验和盘托出。借医生之口,往往能洗刷掉药厂的嫌疑。
另一方面,资助医生进行相关研究,鼓励其撰写某款药物“超适应症”相关文章,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营销手段。王月红在某外资药企医学部任职。她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为医生提供各种学术上的便利。为免曝光,王与记者的见面地点选在了一家隐秘的咖啡馆。据王介绍,医学部的作用便是利用公司资源,为医生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文献资料、循证医学研究结果,以及药物在国外的上市和实际使用情况,以便医生在符合药厂利益的方向上做出尝试。“我们始终强调自己的角色是被动的。只在医生主动咨询的情况下才会告知,绝不落下口实。只要对方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就不能说我们在超适应症推广。”
进退两难
多年来超适应症用药一直屡禁不止,背后除了有经济利益的直接驱动,也有许多令医学界进退两难的伦理困境。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20年前,特雷特博士在一个原本用于改善冠心病的新药临床试验中意外发现了“伟哥”的奇妙作用。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粒蓝色的小药丸会成为“20世纪留给21世纪最有价值、最激动人心的遗产”。
在临床中“歪打正着”并非孤例。《美国医学会会志》曾披露,在美国医院,每年约有40%~60%的处方药被用于“未经FD A批准的用途”。这些未经批准的新适应症被美其名曰为“老药新用”,经过试验甚至最终改变了过去的用途成为了患者福音。例如解热镇痛百年老药阿司匹林被用于稀释血液,防止血栓形成;抗癌老药丝裂霉素被用于治疗白血病;抗菌药甲氧卞氨嘧啶用于治疗艾滋病;避孕药雷洛昔芬被用于预防女性骨质疏松;抗抑郁药物阿托西汀用于治疗儿童多动症都是成功例子。
有医生甚至担心,如果完全堵住了“超适应症用药”的口子,将极大地抑制临床实践的创新。特别是对那些尚无有效药物治疗的罕见病,尝试“老药”可能是唯一的机会。
一些在国外被批准了多重适应症的药品进入中国后,由于高昂的试验成本,只能忍痛割爱,仅选择部分适应症向国家药监局申报,以求先行上市。等日后药厂提供了足够的临床研究资料后再申请追加药物适应症。
这种迂回的办法造成了说明书的滞后,也带来了时间上的真空。一边是等待救命却无药可医的病人,一边却是医生最重要的职业操守,孰轻孰重?
2010年,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眼药门”事件。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对116名患者眼内注射了阿瓦斯汀药物后,有55位患者出现眼部红肿、视力模糊等症状,其中部分患者几乎失明。
阿瓦斯汀是美国第一个获得批准上市的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药物,进入中国后注册的适应症为转移性直肠癌。多种证据表明,在治疗老年黄斑变性(A M D )时,阿瓦斯汀也能显示出良好的效果。如果不使用这种遏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特效药,黄斑变性会很快发展为不可逆转的失明。阿瓦斯汀是仅有的几种特效药里,价格最低廉的,在眼科门诊很受欢迎。事件发生后,阿瓦斯汀被诟病为“超适应症用药”的典型,公众把愤怒的焦点直接对准了医生。
公开的资料却显示,阿瓦斯汀的问题并不出在用药方法本身,而出在了药品制作上。原始包装的阿瓦斯汀为大剂量,而眼科用药则需将其分装成小剂量使用,阿瓦斯汀制剂中不含保护剂,这种操作在医院进行,本来就存在着药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重要的是,阿瓦斯汀并不是按照眼科用药的标准生产,后者在制作工序上更为严谨,这意味着药品的稳定性及质量难以保证。
多年从事生物制药研发工作、医药行业的资深评论员刘伯宁进一步撰文指出,出于商业利益,阿瓦斯汀的生产商基因泰克绝不会主动去开发小剂量的阿瓦斯汀眼科用药,或申请阿瓦斯汀的眼科适应症。因为市面上另一款获得FD A批准、用于治疗A M D的药物———兰尼单抗,同样为其生产。前者的单次费用仅为25~75美元,而后者则高达2000美元。
“姑且毋论开发药物的新型临床适应症,需要重新进行耗资巨大的临床试验,即使阿瓦斯汀的眼科适应症被批准,基因泰克公司得到的也只是兰尼单抗的滞销。”为了保证兰尼单抗的市场份额,2007年基因泰克甚至向美国医学会发出公开信,强烈反对阿瓦斯汀用于治疗眼科病症,并决定不再向制剂公司出售阿瓦斯汀的原料药。
尽管没有合法批文,但出于对患者实际情况的考虑,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医生仍把阿瓦斯汀广泛应用于治疗黄斑变性和其他的视网膜病变,每年可为患者节约近30亿美元的花销。
最后一道防线
理论上被认为对医生处方负有监管职责的药师,近年来其“把关人”的作用也被逐渐矮化了。目前,我国大部分医院里都启用了电子就诊系统。医生在电脑上开药,处方一经提交便可“一路绿灯”直达药房,工作人员只管“照单抓药”即可。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药师吴晓玲从医20余年,深感其中的无奈。“按照系统流程,药师对处方的审核往往发生在患者付费以后。一旦把药方打回去,病人要再去找医生,重新排队,非常麻烦,这种方法实际上已经对医生失去了足够的约束力。”
吴晓玲进一步指出,除了超适应症外,还有一些使用过量或方法不当等超说明书问题也在临床中时有发生。“当时有一款叫奥美拉挫的治疗胃病的药物,说明书写的是一天一次给药,但很多医生开出来的处方写的却是一天两次给药。我们便把药方打回去。医生们过来辩解说,有文献报告一天两次给药效果最好。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后发现,情况并不是像医生说的那样,这种给药剂量只针对糜烂性胃溃疡患者。任何药物用量越大,不良反应越大,这是绝对的。后来经过药师委员会备案后,医生被要求必须把诊断书写清楚。”
为了保护患者和医生的权益,解决超说明书用药的尴尬,2010年3月,广东省药学会印发了《药品未注册用法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这是我国第一次对“药品未注册用法”做出规范。
身为广东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的吴晓玲是参与起草的专家之一。吴透露,一开始,曾有专家提出超说明书用药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没有必要讨论,甚至有人担心这样的规范可能纵容医生或药企过度用药的行为。“但是超说明书用药情况已经非常普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要去‘疏’而不是去‘堵’。”
《共识》中提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 A )明确表示“不强迫医生必须完全遵守官方批准的药品说明书用法”。药品说明书用法往往滞后于科学知识和文献,若“药品未注册用法”是根据合理的科学理论、专家意见或临床对照试验获得的,是为了患者的利益,没有欺骗行为,“药品未注册用法”是合理的。
同时,《共识》亦对临床工作中如何使用“未注册药品”,提出了4个应同时具备的条件:在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或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无合理的可替代药品;用药目的必须仅仅是为了患者的利益,而不是试验研究;有合理的医学实践证据,如有充分的文献报道、循证医学研究结果、多年临床实践证明及申请扩大药品适应症的研究结果等;经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药事管理委员会)及伦理委员会批准。
以上内容被视为医生的最后一道防线。遗憾的是,这份由行业学会发布的《专家共识》仅仅是一份通则,对某个药品未注册用法可能产生的危险或不良反应没有详细交代。临床医生和药师只能凭各自的经验进行补充,缺乏统一的参考,也不具备法律效力。
好在《共识》出台后,民间反响热烈。
受其启发,目前国家卫生部门已经在着手酝酿中国第一部药品未注册用法管理规定,试图让“超适应症用药”早日有法可依。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 周执 实习生 时恩 王洋漾